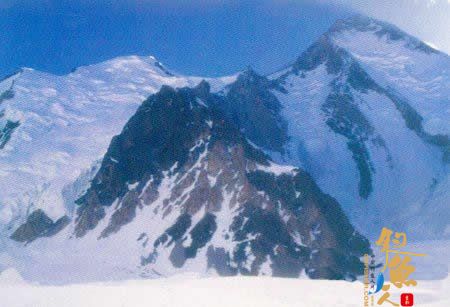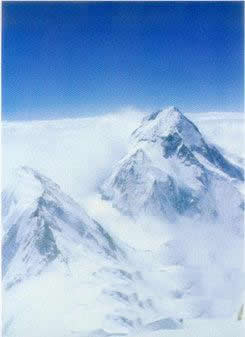上帝偏愛重步兵 翻譯自《Alpinist》Vol.16,Mountain Profile,The Matterhorn 文/Herve Barmasse、Luca Maspe
茨姆特之鼻(Zmutt Nose)
登山家們在北壁上的探索並沒有因為博納蒂的歷史性攀登而宣告結束,仍然有一道難題占據著他們的心思。那就是位於北壁右手邊的一處令人恐懼的巖石山體,因其外形而被稱為“茨姆特之鼻”。它的仰角、嚴酷的自然環境和技術難點,無論是攀冰路段還是馬特洪峰所特有的脆弱的巖石,都使它直至今天依然是登山運動中最艱巨的挑戰之一。
1969年7月,意大利人亞歷山德羅・貢納(Alessandro Gogna)和裏奧・克魯蒂(Leo Cerruti)率先解決了這道難題。此前一年,貢納曾首次以solo的方式完成了大喬拉斯峰沃克山脊(Walker Spur)路線,但在“茨姆特之鼻”,這對繩伴用了四天時間才摸索出如何通過那罕見的仰角、傾斜的支點以及不太可靠的層狀巖體。“茨姆特之鼻”上的第二條路線開辟於首攀12年後,它被認為是這座山峰上最不友好的部分。
圖:裏奧・克魯蒂在1969年首登路上 Photo/Michel Piola
伴隨第二條新路線一起登場的是現代阿爾卑斯攀登的代表人物米歇爾・皮奧拉(Michel Piola),他在Grand Capucin開辟“Voyage Selon Gulliver”路線(譯註:看上去象格利佛遊記的法文說法)時第一次運用膨脹釘把完全不同的裂縫系統聯接在一起,從而引發了一場從艾格爾峰到勃朗峰的技術攀登革命。1981年7月,皮奧拉和皮埃爾-阿蘭・斯坦納(Pierre-Alain Steiner)在堅實的巖石地形上找到一條合理的新路線攻克“茨姆特之鼻”,當時他們曾斷言該路線日後會成為一條可以自由攀登方式在一天內完成的經典路線。不過,這預言至今未被實現。皮埃爾・阿蘭・斯坦納在1981年他和米歇爾・
圖:皮奧拉開辟的“皮奧拉・斯坦納”路線(ED:5.10d、A2,1000米,“茨姆特之鼻”上的第二條路線)上一段開放的繩距。所有攀登“茨姆特之鼻”的人在上巖石前都要先過一段雪坡,存在落石危險。Photo/Michel Piola
可接近性差,再加上客觀存在的危險,之後很多年裏,許多有誌於此的攀登者紛紛打消了親近“茨姆特之鼻”的想法,只有極少數人有幸重復了最早的兩條路線。這種局面隨著阿爾卑斯攀登歷史中最活躍的人物,法國人帕特裏克・“加布”・加巴羅爾(Patrick “Gab” Gabarrou)的到來發生了變化,經過四次獨立的攀登嘗試,他開辟了“鼻子”右緣最筆直的一條仰角路線。
1989年7月上旬,加布和皮埃羅・古爾丁(Pierrot Gourdin)沿“皮奧拉-斯坦納”路線攀登到懸巖底部,後因古爾丁生病放棄。幾天後,加布與弗朗科依斯・馬西尼(Francois Marsigny)搭檔開始了第二次嘗試。他們攀登到了“鼻子”上突起的大懸巖,不過路線全是緊湊的頁巖很難打釘。先是自由攀登,隨後借助了器械。兩人在最大的一塊懸巖底部露營,之後的攀登中繼續被找不到地方放巖錐的問題所困擾,隨後天氣變化,隊伍在強風中結束了攀登,沿茨姆特山脊下撤。
12下一頁申明:本站發佈所有文章、圖片資源内容,如無特殊説明或標注,均爲采集或轉發網絡資源。如若本站所發之内容侵犯了原著者或所有權主體的合法權益,可聯絡本站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