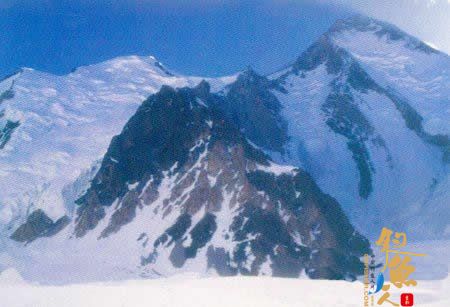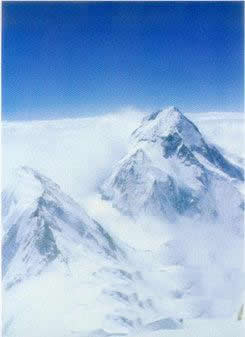上帝偏愛重步兵 翻譯自《Alpinist》Vol.16,Mountain Profile,The Matterhorn 文/Herve Barmasse、Luca Maspes
從博納蒂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1965年,馬特洪峰迎來了首登100周年,眾多攀登者聚焦於此,這其中就有意大利人沃爾特•博納蒂。多年來,他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全能登山家。他決定把在最嚴酷的季節攀登馬特洪峰最艱難的巖壁作為自己攀登生涯的告別演出。
雖然卡斯帕•穆塞爾(Kaspar Mooser)和維克托•伊勃登(Victor Imboden)早在1928年就有過嘗試,但當時還沒有人完成北壁直上路線。博納蒂之前接受過K2和GIV的洗禮,並且在勃朗峰山系開辟了許多新路線,他已經具備了足夠堅強的意誌和足夠高超的技藝,在所有人都失敗的地方獲得成功。他攀登北壁直上路線的想法由來已久,但只是在和搭檔吉吉•佩內(Gigi Panei)、阿爾貝托•塔索蒂(Alberto Tassotti)首次為期三天的嘗試因壞天氣失敗後,他才決定單人完成這條路線。
由於實在找不到人願意陪他再試一次,博納蒂選擇了solo--當然,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媒體早就反復提及直上路線這道“難題”,再加上百年慶典營造出的氣氛,很難保證沒有其他攀登者懷有同樣的想法。於是2月18日那天,博納蒂邀請了三位朋友同行,讓人以為他們只是和往常一樣去滑雪,然後在一塊巨石的掩護下,博納蒂悄悄換上裝備,出發獨自攀登。在經過和孤獨、低溫及技術難點連續六天的拼搏後,博納蒂完成了這道只有極少數登山家曾思考過的命題:單人+反季節+新路線,完成北壁。
圖:沃爾特•博納蒂用反季節solo馬特洪峰北壁直上路線的方式,為自己輝煌的攀登生涯畫上了一個有力的句號。photo/Walter Bonatti
雖然那個時代新出現的攀登器材和攀登技術幫了博納蒂不少忙,但無可否認,他的勇氣、決心和毅力才是成功的首要因素。在親自嘗試重復這條路線後,萊因霍爾德•梅斯納爾說:“我本可以講我下撤是因為天氣變壞,但事實上,我下撤是因為我已無法再向上攀登。那個單人攀上這面巖壁的家夥簡直就是神人。”1994年3月8-11日,女登山家凱瑟琳•黛斯特薇爾(Catherine Destivelle)完成了博納蒂路線的首次重復,而梅斯納爾的話則是對她這次漂亮的冬季solo的重要性的最合適的評價。
Pic Muzio是南壁右手邊一塊高大的巖石柱狀山體。在博納蒂開辟北壁直上路線的同年夏天,萊科•斯派德斯•朱塞佩•拉弗朗科尼(Lecco Spiders Giuseppe Lafranconi)和安尼貝爾•祖奇(Annibale Zucchi)用三天時間開辟了這段立柱上的第一條路線。最初是以器械攀登的方式完成,這條路線,尤其是前半部分巖石質地很差,落石頻發。另一方面,在1970年7月14日,另一支意大利隊--裏奧•克魯蒂(Leo Cerruti)、賈尼•卡爾加諾(Gianni Calcagno)、卡梅洛•迪•佩特羅(Carmelo di Pietro)和高迪奧•馬切托(Guido Machetto)――沿著斯派德斯路線左側一條新路線攀上了巖石立柱,而這條路線的巖石狀況則是罕見的理想(僅就馬特洪峰而言);有觀點認為他們開辟的花兒刃脊(Flowers Arete)擁有這座山上最佳的巖石構造。
十三年後,才華橫溢的斯洛文尼亞隱士弗朗切克•科尼茲(Francek Knez)在斯派德斯路線的左側又開了一條地理特征與之非常相似的新線。“巖石的總體狀況糟糕,但幸好在難點繩距情況比較理想。”科尼茲這樣評價他在1983年6月16-17日和托恩•格魯(Tone Galuh)、圖西克•雅卡(Tucic Jaka)一起完成的新路線――“三個火槍手”。在陡壁下面的平臺,隊伍遭到暴風雪的圍剿,被迫經歷了一場漫長的緊急下撤,穿過東壁的頂端,逃回到“Hornli”木屋。
七十年代初期是峭壁攀登的時代。1972年,登山界再次掀起北壁攀登浪潮。最先是日本人Masahiro Furukawa、Masaru Miyagawa和Yoshinori Okitsu在博納蒂路線的右邊開辟了一條新的直上路線,用了七個營地以及相當可觀的巖釘和膨脹釘。一個月後的8月11-13日,前捷克斯洛伐克人基斯拉夫•德裏克(Zdislav Drlik)、裏奧斯•霍爾卡(Leos Horka)、布赫米爾•卡德西克(Bohumil Kadlcik)和瓦克拉夫•普羅基斯(Vaclav Prokes)開辟了可能是馬特洪峰迄今為止最陡直的一條路線。他們的路線從北壁底部正中央開始,最後250米以幾乎垂直的角度切入施密德路線,至今無人能夠重復,一方面這可能是由於它和博納蒂路線區別不大,另外附近的“茨姆特之鼻”(Zmutt Nose)上也潛在有許多重要的未登路線等待人們去發掘。
1978年一月,來自意大利境內山谷中的當地人重新走上了攀登馬特洪峰的舞臺。在那之前,西壁上總共才有過四次攀登嘗試,這也是馬特洪峰最偏僻、最不被人所了解的一面巖壁。阿爾卑斯向導馬爾科•巴瑪塞(Marco Barmasse)、因諾森佐•米納布瑞茲(Innocenzo Menabreaz)、裏奧•佩森(Leo Pession)、羅蘭多•阿爾貝蒂尼(Rolando Albertini)、奧古斯托•塔蒙內(Augusto Tamone)、阿圖羅(Arturo) 和奧裏斯特•斯奎勒巴爾(Oreste Squinobal)成功地在冬季攀登了達奎因和奧丁於1962年開辟的直上路線,這也是該路線首登後的第一次重復。不過沖頂日那天的暴風雪在布裏耶和策馬特降下了兩米厚的新雪,結果阿爾貝蒂尼在下撤時遇難,一場本因慶祝的勝利轉眼就被傷痛所代替。
盡管這次攀登以悲劇收尾,但是馬爾科•巴瑪塞――也就是作者本人的父親――卻從此開始了他在馬特洪峰瘋狂的冒險。他在這座山峰,尤其是從意大利境內開始,完成了多條新路線和多次冬季首攀,他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只要發揮一點點想象力,就可以找到很多值得去做的新的嘗試。1983年3月10日,他和賈尼•葛雷特(Gianni Gorret)、裏奧、路吉•佩森(Luigi Pession)一起完成了迪法耶山脊路線的首次冬攀。同年9月28日和維托利奧•迪•圖奧尼(Vittorio De Tuoni)開辟了Pic Muzio東南山脊路線,一條巖石質地“不那麽完美”石灰石路線。一天後,雷納托•卡薩洛托(Renato Casarotto)和賈卡羅•格拉西(Giancarlo Grassi)就在南壁開辟了一條直達丁達爾峰下方的垂直柱狀山體路線,然後在第二年的三月,巴瑪塞、葛雷特和奧古斯托•塔蒙內實現了這條路線的冬季首攀。1983年11月13日,他又和迪•圖奧尼、瓦爾特•卡贊內裏(Valter Cazzanelli)開辟了一條新的南壁直上路線,還在頂峰巨石底部約4300米的高度遇見了三只巖羚羊。
1985年9月11日,巴瑪塞用15小時完成單人穿越馬特洪峰四條主山脊:先沿福吉恩山脊上(該路線的首次solo由博納蒂完成),霍恩利山脊下,穿越北壁底至茨姆特山脊登頂,然後從獅子山脊下撤。(七年後的1992年7月19日,另兩位牛人漢斯•卡默蘭德和叠戈•魏利格(Diego Wellig)將這項計劃進一步推向極至,在不到24小時內連續四次登頂馬特洪峰:茨姆特山脊上,霍恩利山脊下,福吉恩山脊上,獅子山脊下,再從獅子山脊上攀,霍恩利山脊下,然後再往返一次霍恩利山脊路線。)1987年聖誕節,巴瑪塞、卡贊內裏和尼古拉•科拉迪(Nicola Corradi)完成了花兒刃脊路線的冬季首攀。巴瑪塞在擔任向導以及作為獨立攀登者期間完成的開拓性探索,真實體現了來自瓦托內切的攀登者們的傳統,他們是馬特洪峰永恒的主角。
對於這段擁有如此豐富的冬季攀登和首登的時期,最後需要提到的一個亮點就是1983年2月21日-3月1日,由來自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米哈爾•皮特卡(Michal Pitelka)、約瑟夫•裏貝卡(Josef Rybicka)和吉瑞•斯密德(Jiri Smid)開辟的北壁新路線。這條新路線始於北壁傳統路線,終於溫伯爾首登時霍恩利山脊路線的山肩部位,提到它,是因為就如同眾多二十世紀末的攀登一樣,它就好象一根紐帶,連接起登山運動的過去和現在。
申明:本站發佈所有文章、圖片資源内容,如無特殊説明或標注,均爲采集或轉發網絡資源。如若本站所發之内容侵犯了原著者或所有權主體的合法權益,可聯絡本站刪除。